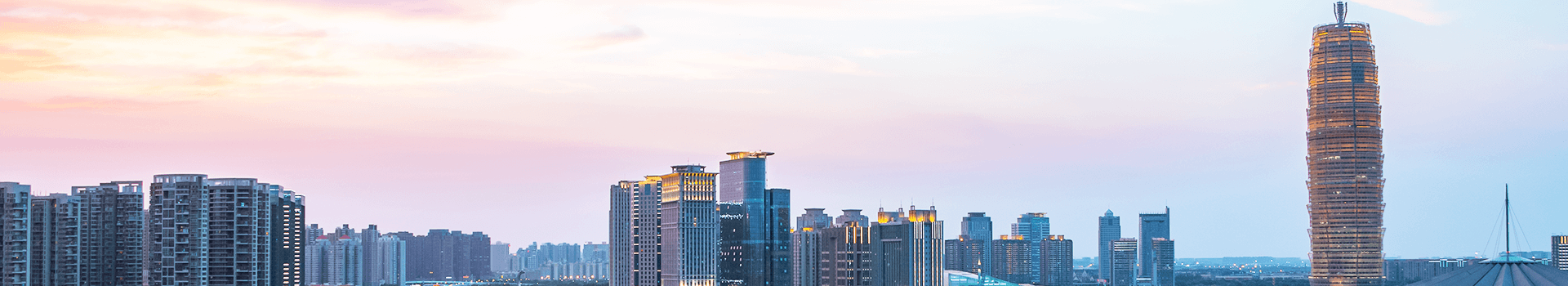你們長(zhǎng)眠���,我們常念——新華社記者追憶扶貧英烈
時(shí)間:2021-04-06 來(lái)源:新華網(wǎng)
? 新華社北京4月5日電 題:你們長(zhǎng)眠����,我們常念——新華社記者追憶扶貧英烈
新華社記者
脫貧攻堅(jiān)戰(zhàn)勝利了,1800多名“戰(zhàn)士”永遠(yuǎn)地留在了戰(zhàn)場(chǎng)�����。
清明時(shí)節(jié),新華社記者回憶那些印在頭腦里的戰(zhàn)士面孔����,說(shuō)一些藏在心底的感慨。
?����。ㄒ唬┠惆?/span>“位卑未敢忘憂國(guó)”寫進(jìn)家書
我清楚地記得�����,余永流是2020年12月1日早晨去世的���。當(dāng)天11點(diǎn)多��,我從遵義那邊得知消息����。

他去世5天后�,我到觀壩社區(qū)采訪。說(shuō)實(shí)話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還有點(diǎn)忐忑,擔(dān)心余永流只是因?yàn)檫@封信火�。
我走進(jìn)貧困戶家。馮先友說(shuō)起他兒子查出血液病后����,一家生活困難,余永流四處奔走��,為他們爭(zhēng)取救助�,兒子病情有了很大好轉(zhuǎn)。姚國(guó)和說(shuō)��,平時(shí)看余永流工作很拼����,沒(méi)想到他孩子那么小,“淚奔�����,一路走好”�。
我采訪他的同事。他們你一言我一語(yǔ):余永流帶他們?nèi)ニ拇◣拓毨艉⒆由蠎艨?、辦低保;為了吸引企業(yè)投資��,他多方聯(lián)系���,還自己畫了圖紙��;五個(gè)多月的茄子銷售期�,他早起到地里督促群眾采摘����,夜里做銷售臺(tái)賬,有時(shí)熬通宵��。
他的妻子吳學(xué)義手機(jī)里保存著一段視頻�����。
“我走嘍��,我走嘍���,你就在這里玩喏���!”
“爸爸——”
鄉(xiāng)間小道上����,女兒左顧右盼玩耍����,余永流開(kāi)玩笑似地呼喚,女兒抬頭����,張開(kāi)雙臂撲向爸爸。
“女兒太小���,她好像已經(jīng)把爸爸忘記了���,這讓我很難過(guò)。”吳學(xué)義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“不到6歲的兒子�,還記得爸爸,有一次老家有人過(guò)世���,棺槨停在外面�,他非要過(guò)去看,說(shuō)‘爸爸在里面’�����。”
我覺(jué)得�����,余永流信里寫“國(guó)之大計(jì)”“不辱使命”����,不是空話套話��,而是他的心聲����。從他的言行看,他是一個(gè)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人�����,有強(qiáng)烈的家國(guó)情懷��,但也是實(shí)干派,他的一生就是“位卑未敢忘憂國(guó)”的寫照�����。
33歲的余永流�、45歲的馬勇、56歲的徐先文……身處全國(guó)脫貧攻堅(jiān)主戰(zhàn)場(chǎng)的貴州�����,這些年我采訪多名犧牲干部的事跡�����,他們的忘我奉獻(xiàn)深深觸動(dòng)我�。沒(méi)有他們,不會(huì)有今日脫貧攻堅(jiān)成果的取得����。斯人已逝,精神永存����。(記者李驚亞)
(二)你是我未曾謀面的大涼山兄弟
“又夢(mèng)到哥哥�����。夢(mèng)里看他一身泥,很難過(guò)……”4月3日��,大雨�,我接到蔣茹倩的電話。

樊貞子(右)在走訪貧困戶(資料照片)���。新華社發(fā)
他們是吳應(yīng)譜和樊貞子夫婦,在全國(guó)脫貧攻堅(jiān)先進(jìn)個(gè)人表彰對(duì)象中���,他們兩人的名字緊緊相連���,犧牲時(shí)分別為28歲和23歲。
2018年12月16日���,人們沿著崎嶇狹窄的公路����,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他們����。那天是他們新婚第40日���。
翻看一張張合影,兩張笑容滿溢的面孔好似兩個(gè)孩子��。他們結(jié)婚登記日選的是“6月1日”�。樊貞子送給吳應(yīng)譜的新婚禮物,是一本用彩筆記錄愛(ài)戀時(shí)刻的紀(jì)念冊(cè)����,充滿童趣。最后��,樊貞子寫上“未完待續(xù)”�����。
在吳應(yīng)譜的農(nóng)村老家���,我看到他的家門前掛著一對(duì)印有“囍”字的大紅燈籠���,旁邊貼著白色挽聯(lián)。那一刻���,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��。

黃文秀與村民一起采摘運(yùn)輸砂糖橘(資料照片)��。新華社發(fā)
算起來(lái)�����,到現(xiàn)在�����,文秀已經(jīng)走了快兩年����。我心生唏噓:4月本是這個(gè)明媚姑娘的生月�。
2019年6月18日那晚,我開(kāi)始追蹤百色市樂(lè)業(yè)縣百坭村駐村第一書記黃文秀山洪中不幸遇難的資訊���。第二天我到一線���,采訪文秀的親朋好友和村民,不舍的感覺(jué)揮之不去:她的美好隨時(shí)間的推移而愈發(fā)清晰��,也讓離去愈發(fā)殘酷���。
文秀的犧牲�����,給家人帶來(lái)傷痛�����。文秀唯一的姐姐黃愛(ài)娟本在外地工作�����,現(xiàn)在回家照顧年邁的父母�。
4日一大早,黃愛(ài)娟和家人一起到陵園�,蹲在文秀墓前,跟妹妹訴說(shuō)家里近況��。
“請(qǐng)代我給文秀送一枝鮮花����。”我拜托黃姐姐。
文秀應(yīng)會(huì)放心�。戰(zhàn)友們懂她。覃蔚峰在她墓前設(shè)計(jì)了一塊漢白玉的扶貧日記雕塑���,那是她扶貧的見(jiàn)證����。
家人也懂她。父親黃忠杰身患癌癥����,愛(ài)女去世后他說(shuō)自己會(huì)堅(jiān)強(qiáng),與病魔斗爭(zhēng)�����,“讓文秀放心”���。他謝絕慰問(wèn)金:“我們不能給黨和國(guó)家添麻煩�����。這些錢,村里扶貧用得上�。”
黃文秀的“接棒者”、現(xiàn)任百坭村駐村第一書記楊杰興告訴我���,村里貧困人口已“清零”���,辦了村集體企業(yè)���,砂糖橘、清水鴨�����、油茶產(chǎn)業(yè)更興旺�。這個(gè)清明,不少村民在網(wǎng)上拜祭她���。

記者何偉(右一)與同事采訪廣西百色市樂(lè)業(yè)縣百坭村新任駐村第一書記楊杰興(中)(2019年7月31日攝)�。新華社記者 徐海濤 攝
我采訪的不少駐村干部��,提到文秀的影響��,不是因她犧牲�����,而是她的純粹和投入����。比如����,她的扶貧日記繪制了村“貧困戶分布圖”��,密密麻麻標(biāo)注著住址���、家庭情況���、致貧原因等。有人問(wèn)文秀���,為什么要放棄在大城市工作的機(jī)會(huì)����,回到家鄉(xiāng)��?她回答:“總是要有人回來(lái)的����,我就是要回來(lái)的人���。”
我采訪得知��,今年1月�,百坭村村委換屆選舉時(shí),多了3張年輕的新面孔����,他們是主動(dòng)回村的大學(xué)生,想向榜樣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。他們接過(guò)文秀的接力棒����,踏上嶄新征程����。我想,文秀知道了����,會(huì)高興。(記者何偉)
?���。ㄎ澹┠銈兪鞘刈£嚨氐膽?zhàn)士
我當(dāng)記者5年多,跑了5年扶貧。
云南曾經(jīng)的四個(gè)集中連片特困地區(qū)����,都有倒下的扶貧干部。

2019年��,吳志宏(右二)在村民家中走訪����。新華社發(fā)
吳志宏,在滇南的紅河州史志辦工作27年后�,前往紅河縣三村鄉(xiāng)駐村扶貧。在這個(gè)哈尼族聚居的貧困鄉(xiāng)�����,他忙著改造危房�����、解決用水困難�、發(fā)展產(chǎn)業(yè),顧不上對(duì)家人噓寒問(wèn)暖��,更別提團(tuán)聚:妻子食用野生菌中毒����,他沒(méi)有回去;駐村近20個(gè)月�,他幾乎沒(méi)給讀大學(xué)的兒子打電話,微信交流也很少�;與父親居住的小區(qū)一街之隔,但他去世那年只回家兩次���,見(jiàn)父親一次��。他突發(fā)腦溢血那天是10月17日��,國(guó)家扶貧日���,我不會(huì)忘記。75歲的吳爸爸說(shuō)����,他覺(jué)得兒子沒(méi)有離開(kāi),因?yàn)閮鹤泳璜I(xiàn)的器官幫助3名器官衰竭者重獲新生�����,2名失明者重見(jiàn)光明�。
王秋婷(右)到貧困戶家里走訪(資料照片)�����。新華社發(fā)

吳國(guó)良(右二)與扶貧干部交流工作進(jìn)展(資料照片)�����。新華社發(fā)
吳國(guó)良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過(guò)中學(xué)老師���、村支部書記,最后一個(gè)職務(wù)是昆明東川區(qū)湯丹鎮(zhèn)扶貧辦副主任��。他的公務(wù)車輛墜下深溝后�����,我采訪他的父親�、弟弟、妻子�,后來(lái)他全家都成了扶貧隊(duì)員。父親年近花甲��,老黨員,說(shuō)“兒子是他的榜樣”���,一直在村里干扶貧��。妻子原來(lái)是鎮(zhèn)上普通職工,后來(lái)到鄰村扶貧�。弟弟本在外地工作,吳國(guó)良去世后�,他也回到東川扶貧,說(shuō)“完成哥哥未竟的使命”��。
我采訪過(guò)近10位犧牲的扶貧同志���,最小的26歲���,最大的近60歲,有漢族����、彝族、納西族等����。他們大多沒(méi)有轟轟烈烈的事跡�,就像一個(gè)個(gè)戰(zhàn)士���,守在一個(gè)個(gè)陣地��,必須攻下貧困這個(gè)堡壘�����,哪怕“5+2”“白加黑”����,都不會(huì)停下腳步���。
正是這些戰(zhàn)士���,通過(guò)自己的點(diǎn)點(diǎn)滴滴,積年累月�,拉近了共產(chǎn)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聯(lián)系,這不就是初心嗎����?
我記錄他們,是做好記者的本職�。同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我也是作為一個(gè)普通人��,與他們的身邊人相處聊天��,安慰幫助��。(記者楊靜)
(六)你是百姓盼歸的燕子
4月3日晚���,大源村的駐村干部劉云慧發(fā)來(lái)信息:村民今天又自發(fā)祭奠了詩(shī)燕書記��,現(xiàn)場(chǎng)讓人止不住眼淚�����。

記者周楠(左一)與同事在湖南省炎陵縣大源村采訪村民(2月2日攝)�。新華社發(fā)
之所以說(shuō)又���,是因?yàn)?/span>1日已有20多名村民祭奠過(guò)他���。我打電話過(guò)去�����,劉云慧聲音低沉����,還在哀傷中����。

黃詩(shī)燕(右)到湖南炎陵縣大坑村(今大源村)走訪貧困戶(2016年4月6日攝)。新華社發(fā)
白天����,大源村50多名村民,上至70多歲的老人��,下至五六歲的娃娃���,帶著自家釀的米酒���、山上采的杜鵑,匯聚到“燕歸路”上����,追思湖南炎陵縣委原書記黃詩(shī)燕���。
大源村是黃詩(shī)燕生前的脫貧幫扶聯(lián)系村。曾經(jīng)����,大源村人用了17年打下路基,始終還是條鄉(xiāng)村土路���,晴天一身灰��,雨天一身泥����。在時(shí)任縣委書記黃詩(shī)燕的大力支持下���,這條路2017年硬化成了水泥路。黃詩(shī)燕因勞累過(guò)度犧牲后��,村民為紀(jì)念他��,將路命名為“燕歸路”��。
71歲的張艮花蹲在路碑前,慢慢倒上三杯酒�,淚水劃過(guò)臉上的皺紋,“黃書記�����,我?guī)O女來(lái)看你了��。我不會(huì)說(shuō)話�����,但我們世世代代都會(huì)感謝你���,記得你�����。”
村民的講述��,讓我想起2019年黃詩(shī)燕去世后去采訪的情形�����。
在我國(guó)基層黨政權(quán)力體系中��,縣委書記責(zé)任重大��。要做縣委書記的報(bào)道��,挑戰(zhàn)比較大����,我們也有些惴惴不安。
我當(dāng)了10年的“三農(nóng)”記者�,與村民打交道比較多。這些村民平時(shí)面對(duì)鏡頭都緊張���,如果多拍幾遍�,還會(huì)手足無(wú)措�����。但在講述黃詩(shī)燕時(shí)�,我見(jiàn)到了最生動(dòng)�、最放松、最真切的他們�����。
有人緩緩講述、默默流淚�����,有人娓娓道來(lái)���、泣不成聲����,有人剛剛還沉浸在溫馨的故事中��,下一秒?yún)s手捂著臉�,痛悔最后一次見(jiàn)黃書記時(shí)明明看他臉色不好,手掌冰涼��,卻沒(méi)有提醒他去看醫(yī)生�。
采訪后,我在房間走來(lái)走去����,思考:這位縣委書記,到底是做了什么�,才會(huì)讓老百姓如此親近和懷念?
整理筆記�����,我嘗試列出答案:老黃牛、父母官��、家里人����。
炎陵地處全國(guó)14個(gè)集中連片特困地區(qū)之一的羅霄山片區(qū)。2011年起9年時(shí)間��,黃詩(shī)燕帶著大家把黃桃種植面積從5000畝增加到8.3萬(wàn)畝�,4811戶貧困戶因此穩(wěn)定脫貧。他不喜歡拋頭露面��,但為了黃桃銷售����,屢屢“站臺(tái)”當(dāng)推銷員,百姓都說(shuō)“大黃抓小黃���,抓出金黃黃”��。
2014年��,炎陵縣有1.49萬(wàn)戶住房存在安全隱患�,需投入6億元�,而當(dāng)年全縣財(cái)政收入僅7億元。黃詩(shī)燕發(fā)“狠話”拍板:砸鍋賣鐵�����,也要讓老百姓住上新房�!
易地搬遷貧困戶張連軍說(shuō):“黃書記3年來(lái)我家19次,怕我們搬下山不習(xí)慣�����,還給每家配備雜房和菜地�����,什么事都給老百姓考慮到�,真的比親人還親。”
他叫詩(shī)燕����,也如燕子銜泥般壘起了老百姓的“幸福窩”。他去世后��,老百姓對(duì)他自發(fā)的悼念�����,讓我深切理解了“政聲人去后”的含義。
不止黃詩(shī)燕�,脫貧攻堅(jiān)的“一線指揮官”縣委書記群體里還倒下了姜仕坤、澤小勇����、蒙漢……老百姓會(huì)記得他們。(記者周楠)
扶貧英烈已化身青山綠水�,我們能做的就是經(jīng)常想念,接續(xù)奮斗��。(執(zhí)筆:熊爭(zhēng)艷���、屈婷)